文|刘荒田
谈“归来”,出于惯性,第一个想到的,是贺知章的诗: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未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喜悦和尴尬参半,几乎适用于所有归人。
其次,想到宋之问的“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”,它无疑比前一首更深入,触及难以言状的忧虑。
美国人罗伯特·威尔斯所著《来自南中国海底部的呐喊——尚未披露的来美中国移民最大海难纪实》一书,记载了1873年间在太平洋航行一个月、从旧金山到香港的邮轮上的一幕。船越来越靠近中国的海岸,连海湾里的垃圾和岸上耕作的身影都清晰可见,“一大帮中国苦力从统舱拥上来,为的是要看最先出现的陆地。他们去国以后,在加州待了很久很久了,终于看到故国的岸。几个人问我:‘这是中国吗?’我说是,他们发出微笑。然而,其他人冷冷地坐着,竭力抑制自己,不露出任何表情,一个劲儿地压低声音谈话。悬崖近了,更近了;拂晓时分的天光益发明亮,空气益发清澈。他们依然不动声色地坐着,都对别人的举止毫不在意。”
他们去国至少八年,音讯全断,家乡的亲人生死不明,还有没有家也是疑问,极度的牵挂造就的冷漠,令旁观者难以理解。
这是“不敢问”的传神写照。
好曲不厌三天唱,舍去传颂千年的诗句,如果以现代语言描画归来者的特殊心理,那就要借一句流行语:“出走半生,归来还是少年。”这只是祈愿,是不是时光真的倒退为“少年”,须看造化。
但我武断地说:“出走半生,归来‘必是’少年。”只要符合这样的前提:小时候出走,晚年归来,中间有漫长的间隔。
要问道理何在?因为这是普遍的人性。
西哲为了强调童年经验的极端重要,说人的下半生,心灵所做的主要功课,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“回去”。回到哪里去?从哪里出走,哪里就是目的地。
同理,每年除夕,从城市赶回老家吃团圆饭的千千万万打工者,家乡于他们来说,四季只剩一季——冬天,因为另外三季皆在外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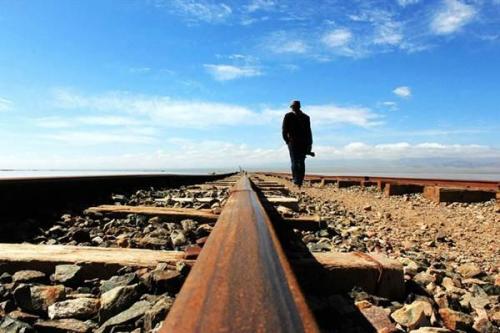
因为故乡于你,全部意义都在“半生”之前的少年。出走以后,你的历练、你的社会关系和故乡脱了钩,如果说和它“斩断骨头连着筋”,也只是他乡见到的泪汪汪的“老乡”,而不是埋着先人骸骨的家山,以及母亲常常依闾盼望你的村子。
少年的一切,从榕树上的鸟窝、知了到锅台上的荷包蛋,从流鼻涕的伙伴到朦胧的初恋,都潜伏在窗棂下,一旦你拧亮一盏煤油灯,它们就会苏醒,向你扑来,让你晕眩。在故乡,只有这样的参照物。所以,哪怕持杖,你被孙子搀扶着,站在童年扎猛子的小河旁边,你下意识地脱衣,作势跳入六月滚滚的“龙舟水”。
以上三种状态,有一共同点——感兴都来自近似的切口——靠近或者刚刚回到家乡的时刻。
久别累积的情愫如炸药包,被“进家门前后”这一可遇不可求的“引信”点燃,淋漓尽致地爆了,爆出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。
然而都命定短暂,大抵是一次性的,原因是,“回来”的瞬息诗意在现实中被消解了。
游子和亲人拥抱,互道别后、哭个痛快以后,便要和满目陌生周旋:
怎样给乡亲送礼,其间要讲究辈分和人情账;
怎样对付难以企避的脏、蚊子和苍蝇;
怎样调和“衣锦还乡”和经济实力的矛盾;如何摆平各种陈年恩怨……
待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儿童把你引进家门之后,即使排除“不敢问来人”一说中蕴含的家破人亡,你也未必会一鼓作气地把乡愁当家乡美食,吃了又吃。
新闻线索报料通道:应用市场下载“齐鲁壹点”APP,或搜索微信小程序“齐鲁壹点”,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!

